毫无疑问,在科学管理控制下,核医学检查完全安全可控。但“恐慌”反应也折射出了大众对这门学科缺乏理性认知的现状。事实上,无论是普通的公众,还是从事相关临床工作和研究的医生们,大家对于核医学的认识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。同时,因为我国核医学起步较晚,核医学产业较发达国家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只有加快核医学相关知识的普及与临床学科更好的融合,才能有效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。
那么核医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科?未来又将面对怎样的发展方向? 近日对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徐浩教授进行了专访,徐浩教授已在核医学领域深耕30年有余,从他的洞见之中,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这门学科,并得以窥见未来核医学的发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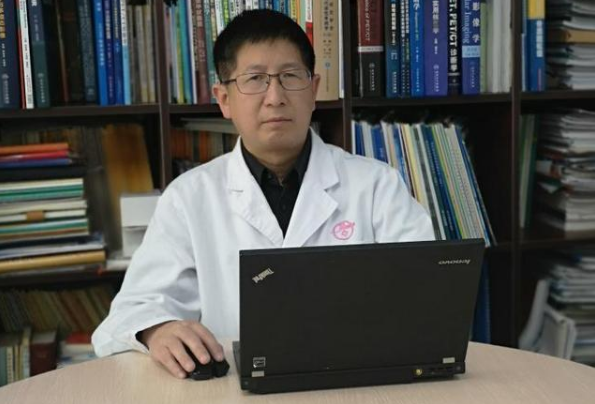
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徐浩教授
核医学是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诊疗工作的桥梁
与CT、MR影像的成像原理不同,现阶段的核医学检查融合了PET及CT(或MR)两种设备。患者在进行检查前将被提前注射放射性药物(示踪剂)。该示踪剂通常反映生理或病理生理状态下的代谢、受体和功能变化。“进入人体后的放射性示踪剂(如18F标记的葡萄糖类似物FDG)1小时左右达到分布平衡。与正常组织或良性病变相比,肿瘤病灶处的代谢会出现异常。因此,体外PET接受到的射线量在肿瘤病灶与正常和良性病变之间也会存在差异,这个时候我们再用CT进行定位,就能精确获取肿瘤的葡萄糖代谢情况。”徐浩教授介绍。
随着核医学朝着精准医学的方向发展,示踪剂的作用逐步加深,针对不同肿瘤病灶的示踪剂逐渐出现,如FDG的葡萄糖代谢显像、NaF的骨显像、FMISO的乏氧显像……示踪剂的发展为精准医疗与核医学的融合铺好了道路。
不过,困难也正值于此:为了针对不同的疾病、不同的病灶进行特异性显像,研究人员必须找出合适的靶点并配以具备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。在这个过程中,放射性药物的研发与创新药的研发有相似之处,研发人员需要从成千上万个药物之中寻找到符合要求的药物,同时还需在临床实验中保证药物的安全性。
这是一个高成本,高时耗的过程,需要研究人员查阅大量的文献,从基础医学研究之中寻求新型放射性药物的踪迹,进而找到可能的化合物进行开发,进而投入临床实验之中,这个过程贯穿了基础医学与临床研究两个环节。在徐浩教授看来,核医学是连接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诊疗工作的桥梁。
但挑战自然也携着机遇,许多药企正朝着核医学科医生的需求不断进发,例如GE药业便因此开发了GE-180示踪剂等能够在临床之中表现出明显特性的专利药,有效推动了示踪剂的研发进程。
示踪剂制备正走向自动化
除了放射性药物的研发之外,制备同样是医院常常面临的一个难题。
“不同的核素具有不同的半衰期,而一旦核素质量发生衰减,它的显像效果将受到极大影响。PET显像常用的放射性核素18F,它的半衰期仅有109分钟,我们必须卡准时间提前准备,在患者进行检查前及时制备。”徐浩教授解释到。
“医护人员的辐射安全是第二个问题。长期与放射性物质相处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。过去的核素往往是由医生手动制备,这意味着医生存在被辐射的风险。同时,示踪剂制备的化学反应控制存在一定的技巧,需要关注众多反应因素,如果在制备时漏掉某些细节,可能会对放射性药物的显像质量产生影响。”
为了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,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采购了GE的小型回旋加速器及全自动化学合成系统(如FASTlab2),他补充到“回旋加速器的小型化让我们在制备药物时对空间的选择上更为灵活,而全自动化学合成系统则能将过去医生的部分操作自动化,对于许多示踪剂的制备,该系统均有成熟的卡套式解决方案,能够大幅提高示踪剂制备的质量与效率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,从手动到现在的半自动,再到未来的全自动,放射性示踪剂的制备问题正被一步步解决。”
核医学走向何方?
总的来说,影响核医学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影像设备与放射性示踪剂。随着我国核医学影像设备审批的不断松绑,未来核医学影像设备的全国装机量将会不断增多,核医学科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增大。
剩下的问题便指向了放射性示踪剂。尽管顶级医院与制药企业都研发了许多新型的放射性药物,但其应用范围仅适用于研发所在的医院内。事实上,我国已经20年没有新的放射性药物出现,放射性药物的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。这需要制药企业、核医学科专家与政府药物审评中心共建对于核医学的新共识。
“下一步,我希望我们能构建发达的放射性药物产业,将放药的制备问题、新药研发问题与可及性问题彻底解决。同时,我们也需要推动核医药诊疗一体化的发展,加速治疗型核素研发,这是核医学与精准医疗结合重要的一步,也是中国核医学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重要一步。当然,这仍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。”在采访的最后徐浩教授强调。
美国前防长佩里:目前发生核战争或核事故可能性比冷战时期还要高